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,我有很久沒(méi)回老家了,縱使過(guò)了好幾個(gè)理應(yīng)回家的節(jié)日。不是不想回,而是回不去。還好,自4月30日起,京津冀三地將重大突發(fā)公共衛(wèi)生事件應(yīng)急響應(yīng)級(jí)別由一級(jí)調(diào)整為二級(jí),出京返京不用雙向隔離了,才使我有了回家的“勇氣和魄力”,呵呵。
沿著又大又廣的免費(fèi)高速一路南插,寶馬良駒風(fēng)馳電掣,讓我真地找到了1200年前太白先生“朝辭白帝彩云間,千里江陵一日還”和子美先生“即從巴峽穿巫峽,便下襄陽(yáng)向洛陽(yáng)”的美妙感覺(jué)。
然而,這感覺(jué)也就才僅僅半天,就消失殆盡。為什么呢?
因?yàn)?,?dāng)我出金灘鎮(zhèn)高速口經(jīng)106國(guó)道回家時(shí),突然有種悵然若失的感覺(jué)——我們娘娘廟村南口馬路邊那兩棵偉岸挺拔的大楊樹(shù)怎么不見(jiàn)了?嗯?
那兩棵高大的大楊樹(shù),是娘娘廟村的標(biāo)志物,是我們村幾代人的心靈保護(hù)神。如今,猛然間不見(jiàn)了,感覺(jué)真的很失落、很悵惘……
或許早已被砍了,只是我久不回家,沒(méi)有注意到而已。問(wèn)及家人才知,我在北京讀書時(shí)已經(jīng)被砍掉了——也就是說(shuō),大楊樹(shù)離開(kāi)我們將近30年了。哎!我的天啊!
大凡上世紀(jì)80年代之前出生的村民都會(huì)清楚地記得,在娘娘廟村南寨門京廣線106國(guó)道北側(cè)460公里處,有兩棵高聳入云的大楊樹(shù)。說(shuō)起來(lái),應(yīng)該有近百年歷史了,記得上世紀(jì)70年代末期生產(chǎn)隊(duì)還未解散,我和一群發(fā)小經(jīng)常在楊樹(shù)下玩耍,附近就是我們第19和20生產(chǎn)隊(duì)的大院,院內(nèi)有糧倉(cāng)、糧場(chǎng)、牲口棚、大馬車、草料場(chǎng)、秸稈垛以及各種農(nóng)具。記得秋收后分糧食或紅薯的時(shí)候,感覺(jué)甚是震撼,在院里看著高高的像小山一樣的紅薯堆一會(huì)兒就分完了,分到每家手里并不多,當(dāng)大人在排隊(duì)過(guò)秤分東西時(shí)我們就到大楊樹(shù)下玩去了。第一次見(jiàn)到大楊樹(shù),就驚詫于它們的高大和威猛,清楚地記得和玩伴們一起丈量它倆的“腰圍”——要三個(gè)小伙伴合圍才能分別摸到對(duì)方的手指,臉肯定是看不見(jiàn)的,很難想象它倆有多少年頭了。
小時(shí)候最喜歡爬樹(shù),村南林場(chǎng)果園里啥樹(shù)都有、也啥樹(shù)都爬過(guò),但對(duì)于它倆,由于抱都抱不住,更不要說(shuō)爬了,著實(shí)讓我們這些“樹(shù)蟲”望樹(shù)興嘆。而且,這兩棵楊樹(shù)雖然由于年齡久遠(yuǎn)的原因都很高大,但也有所不同,西邊那棵雄偉高大,也明顯粗壯一些;東邊那棵稍微苗條一點(diǎn),但也能與之比肩而立、傲視群雄,大有巾幗不讓須眉之勢(shì),給人以“算人間知己吾和汝。重比翼,和云翥”的感覺(jué)。
上小學(xué)四五年級(jí)時(shí),由于我家住村西,村小學(xué)在村東,大楊樹(shù)是我每日必經(jīng)之地,當(dāng)時(shí)它倆對(duì)我來(lái)說(shuō)就是路標(biāo)和地標(biāo),行經(jīng)此地就知道還有一半路就到家或?qū)W校了。每到楊樹(shù)下,微風(fēng)起處,兩棵大楊樹(shù)的大葉子嘩啦作響——好像在給我鼓掌加油,抑或是催我不要磨蹭快點(diǎn)趕路——總之,一到這里聽(tīng)到樹(shù)葉嘩啦聲,我定然會(huì)抖擻精神,必會(huì)加快腳步或者小跑通過(guò)。
曾幾何時(shí),大楊樹(shù)也是娘娘廟村的驕傲——放眼四外其他各村,沒(méi)有哪村的樹(shù)比它倆大或久——也就除了縣城的老槐樹(shù)吧,呵呵。上世紀(jì)80年代初,我家在村西的馬路邊蓋了新房,那些南來(lái)北往的商賈旅客,操著南腔北調(diào)的口音,在我家門口喝水歇腳,許多不知道我們村名的,都不約而同地告訴親人或同伴在有兩棵大楊樹(shù)那個(gè)村的樹(shù)下等,便于見(jiàn)面集合。遇有驟雨或烈日,由于大楊樹(shù)樹(shù)冠直插云天,大如兩把巨傘,倒也成了路人緊急避雨或乘涼歇腳的好地方——它倆那無(wú)數(shù)的大葉子給了無(wú)數(shù)人以無(wú)私的庇護(hù)。
及至到鄉(xiāng)里和縣城讀中學(xué)的時(shí)候,由于上下學(xué)來(lái)去匆匆,且天天在學(xué)校“報(bào)數(shù)”,實(shí)是沒(méi)有時(shí)間和興趣回家后再去“抱樹(shù)”了。而且,因?yàn)槲壹易〈逦?,從?shù)下經(jīng)過(guò)的機(jī)會(huì)也少多了,只是偶爾去村里走親訪友才會(huì)一睹它倆的風(fēng)采。而自從到外地讀大學(xué)和工作,更是很少?gòu)臉?shù)下經(jīng)過(guò)了,但大楊樹(shù)已經(jīng)深深地扎根在我心里,直到如今每每想起它倆,還很是感懷,但從沒(méi)想過(guò)它倆已經(jīng)不見(jiàn)了。
不知為何也不知具體什么日子,它倆就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,幾乎沒(méi)有人再談到或提及,村里人對(duì)大楊樹(shù)的印象漸行漸遠(yuǎn),90后或更小的孩子們更是一無(wú)所知,問(wèn)起來(lái)大都一臉發(fā)懵。
然而,大楊樹(shù)在我心里,卻漸愈高大漸愈清晰也更加神圣起來(lái),它倆那嘩啦啦的掌聲時(shí)時(shí)響徹在我耳際,像是提醒我任何時(shí)候都要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,任何時(shí)候都要堅(jiān)忍不拔、雄起奮進(jìn)。
嗯嗯,那嘩啦啦的掌聲,就像歌里唱的那樣——掌聲響起來(lái),我心更明白,你的愛(ài)將與我同在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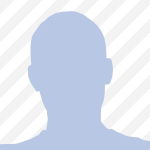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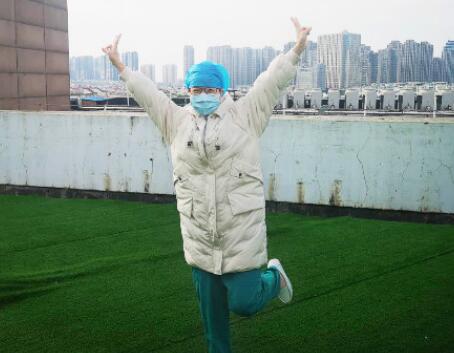



評(píng)論